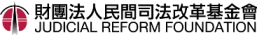最後編輯日:2023年12月6日
正確而有效的通譯是基本人權
一個聽不懂法官、檢察官或律師,或其他在法庭上的人在說什麼、問什麼的當事人,如何做充分的說明,為自己辯護?
難道只有會說這個國家的語言,才有機會為自己、為正義辯護嗎?
當一個人站在法庭上,卻聽不懂任何一句對話,正義的天秤是否從一開始便已傾斜,因為人民連完整表達意見、主張權利甚至了解整個法庭活動的機會都沒有。
依據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》第14條第3項對被告之最低限度程序保障規定:「第1款: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,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。第2款: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,準備答辯,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。…第6款: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,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。」
我國的《法院組織法》第98條也規定:「訴訟當事人、證人、鑑定人及其他有關係之人,如有不通國語者,由通譯傳譯之。」
當人民不能通曉法院所使用之語言時,有權運用正確、有效的通譯是獲得公平審判所不可或缺之要件,因此,通譯的有無很重要,而且可以主動要求、爭取通譯也很重要。此為兩公約所明訂的基本人權,亦為國家的當然義務。
現行通譯制度之問題
民間司改會開始關注通譯問題,源自於長期推動的法庭觀察活動。其中,法庭觀察員發現法院的通譯普遍「既不能譯,也不會通」,部分通譯甚至連一般台灣社會中經常使用的台語、客語,也出現雞同鴨講的狀況。通譯在法庭上的工作幾乎只是負責按下錄音機或轉交證物,部分通譯甚至還狐假虎威,比法官還兇。
語種不足
部分語種,包括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3條明訂應延攬語種(葡萄牙語),及原已建置之印地語、雲南話等語種,均因法律專業之通譯量能不足,未接續建置,致須聘請臨時通譯協助傳譯
通譯服務語種及備選人數數據資料統計
| 106年度 | 110年度 | |
| 語種數量 | 20 | 232 |
| 特約通譯備選人人數 | 21 | 271 |
資料來源:監察院110年決算報告
特約通譯傳譯服務情形意見反應表及評量表不具準確參考價值
110年度1至8月各法院運用通譯人員傳譯案件計5756件,意見表及評量表回收、陳報情況統計如下表,值得注意的是,意見反應表及評量表之數據,部分法院未全數陳報,或陳報數大於回收數,並非完全具有準確的參考價值。
特約通譯傳譯服務情形意見反應表及評量表回收、陳報情況統計
| 意見反應表 | 評量表 | |
| 回收件數 | 222 | 1596 |
| 占通譯案件比率 | 3.86% | 27.73% |
| 回收掃描陳報、上網填報件數 | 135 | 1300 |
| 占通譯案件比率 | 60.81% | 81.45% |
資料來源:監察院110年決算報告
人力之不足與利益衝突
由於法庭所設的通譯有時沒辦法發揮功能,導致真正遇到需要通譯的狀況時,反而是由職司逮捕的外事警察直接擔任所捕被告之通譯,或是由陪同當事人出庭的社工人員來當臨時翻譯,甚至讓仲介擔任移工的通譯。有違通譯公正中立義務,且仲介與他所仲介的移工之間則可能有利害衝突,如此作法顯然急需改善。
通譯翻譯的品質
本會曾於2021年底舉辦有關通譯制度的座談會,其中與談人提及有時通譯會憑著自己的意識去增、減翻譯提問內容,可能導致移工未接收到法官或檢察官真正的意思。當通譯在法院或執法單位、警察局、派出所或移民署,用自己的意思告訴當事人,再以通譯的意思做回答,或有時通譯擔心未回答到問題的重點、或翻譯時間過長會遭到責備,以自己的意思解釋問題或答辯,這樣的操作下將嚴重影響通譯的品質。
再者,多數通譯僅有在法官或檢察官問被告話時才會進行翻譯,但正確來說,法院進行的整個程序都應該完整翻譯給被告聽,否則除了輪到被告陳述時,被告就好像是法庭的孤兒,連目前正在發生什麼都無從得知。
制度、資源分散
台灣沒有固定的通譯養成制度,訓練、認證及評鑑制度亦缺乏統一標準。僅是官方就有兩套不同特約通譯制度,分別為內政部通譯人員資料庫以及法院的約聘辦法,兩者的資格要求亦不同。
內政部設立的通譯人員資料庫之要求是不同於法院的,前者是經過公部門、大專院校、民間團體,其一的訓練及考試,並取得證書即可成為通譯人員 ; 後者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的要求較為嚴格,門檻也較高,並須經過法院書面審查及到法院上課,如法院業務簡介、法律常識及審理程序相關的規定,還有專業技能及倫理責任等課程,法院亦可增加課程時數,且通過後,建置於法院資料庫之有效期限僅有兩年,然而,同一人在不同地區的登錄,在資料庫裡卻視為不同人,造成同一語種之通譯人員資料庫名冊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重複的,顯見資料庫的登錄未對人員身分實施詳細的驗證。
政府實際作為
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曾就司法通譯制度做成7項決議,包括增加通譯人員培訓經費、辦理各級語言檢定、建立司法通譯人才資料庫等項目,陸續推動通譯制度改革。但目前,仍有諸多問題待改善:
- 目前通譯名冊散見於司法院及各部會,不利當事人查詢相關資訊,應致力於跨單位人力、資源整合,使資訊集中呈現於司法院或法務部網站,改善人民查詢不便之困境。
- 落實完整教育訓練及認證標準,尤其針對法律名詞、專業術語、公部門處理相關事件的程序以及文化差異之了解,並由司法院統一規範認證標準,以免通譯品質參差不齊、難以監管
- 為因應台灣多元社會組成之特殊性,司法院官網宜設計多國語言供人民選擇瀏覽,並確保各語種版本網站資訊提供之一致性
- 設計多國語言之通譯制度「使用後意見反應表」,充分利用當事人本國語言之「意見反應表」及「評量表」了解當事人通譯資源使用狀況
- 增設完善通譯迴避制度及倫理規範相關法律,以防免惡質仲介成為外籍人士通譯,更不利其保障